◎更多时候我们会到江边去吹风
从甬道流往滩涂,荒蛮的白色泡沫上,坐着
奋力摇撸的人。且颂赞歌,喘息以江河
假歧义,筑光阴吟另一部《怀沙》
上声读遍。谱系棕黄的苟且笃行着苟且
祭往汨罗汤汤之水的便不是屈子
仓促的龙舟和黄酒来不及落泪,一日仓促
雕不完祝祷家国的冠语,更
肃不尽刻意误读出高歌长虹的江上舟楫
你知道,冤你者比你更懂你委屈
你也知道,噩噩者逐波必不懂你
你投不回两千三百年前的江
你也镀不出商女逶迤后庭花的卓卓金身
你被悲悯困住的灵魂羁绊了肉身
你举杯在风里,轻念:安康
“一匹马,顺着甬道奔袭
月光越过你的肩膀,洒了满地
满地槐香便也睡去……”
◎我把年少时光的回忆煮在饭里
雪,并非失约
在异乡
粉紫色三角梅爬满骑楼的老街上
形容北方的词,总是
像匆忙中
被时光遗失的我
车、马、邮件
一餐、一饭
总能慢过木心的诗
慢过
叮嘱和期冀
缓缓地
在味蕾间酿出
取悦记忆的全部嗜好
◎我是一朵睡着了的火焰,来到你家乡
我,是一朵失眠的花
燃在黑乌乌的胡笛声里的红蓼
会趁季河涨水
饱饮奢欲,开出
成穗的胭脂与寂寞
我,是浓夜里的莲
是你点染星子时惊扰了我
安眠红尘的
半生独孤片片瓦解
你说废墟上翠绿的莲心可解世人的心毒
我,是倚上枝梢的浅盼
朝颜的号角
集结成蜂蝶的嘤嗡与爱慕
虚弱着
七月湿热的雨与成熟
我,是初春
尚未苏醒的瑞香,隔着女校
郎朗书声阅读清风燃退的同里古镇,退思
一步一摇的折扇内
暗藏了火种
◎被风吹老的事物记忆犹新
七月云层再次显露龟裂,它们——
“好小啊”一栋无法称为楼宇的建筑,一段不肯承载回忆的静物
又或者只是一席雨、一弯河、一封晨夕、一套马车
从那个转角走来。“要,再来一杯吗?”
你坐在角楼下的露天酒吧,仿佛在等一杯马提尼
又仿佛不是,你只是等晚霞撑起残杯,可
这等待已持续了好几个光年
◎唤醒一条河流
当承诺无法弥合时
她把门推上了
一点一点行走在库索图阿
雪后泥泞的路上
丈量正如倾斜的风标
把长长的影子投向正渐渐出离的
黎斯凯基山脚
其实这些并不重要,我
只是杜撰了开篇
在真正的魁北克,唯一筑有城墙的回忆中
圣劳伦斯河上飘荡着的才叫眼泪
而那个故事短促得令人心疼
所以,我还是继续
讲我假设的城
她从某个初冬离开了他,和
那间用黄油、谎言、苹果酱、爱和冰冷交织的房子
◎冬天的,春天的,同夏天的一样的,我讲树
种植
它便真的与我一样
惧怕生枝,繁衍
唯有依托逃亡来拯救
我,就要死了,终止这无休止的喧哗 [img=800,240][/img] ◎在老虎身上裹一层红布
暗影曾来自捕声者与风的格斗 大马士革纹饰上 打着瞌睡等待火焰的焦糖 槭树翠色高光,以及 温莎留在瓷碟内渐渐干涸的品红
这些,并不佐证 该更荒诞些的
通常傍晚的地铁,会 刺穿闹市 回到长满曼陀罗花的内陆
深夜 裹在梵蒂冈城猩红色教袍内的拉尔夫哭泣 有关光的预言顺着瑞士卫队脚下的石阶坍塌 乌鸫飞出来 猛犸象奔出来 孟加拉虎冲出来 十难在红布的遮挡下,跃跃欲试
◎他在一部经书中诵读玫瑰
雪泥鸿爪 破云附梦 选在愈发接近时放下 蛛丝的垂坠,总是 轻轻颠簸 将梵唱从水中打捞出来,搁置在 月色围拢的禅堂 于是 入木的菩萨 被从树心拉出,留下满身刻痕 花香被沉潭 纤纤缕缕绕紧木鱼的晚课 一声,两声,千百声,静无声……
◎我们住在绿叶上
那一天 来自珠科河的雨 终于停下来 留下 依旧炎热的傍晚 岸边 前几日躲进草窠子的孑孓 业已成年 也该飞出觅食了 而我们 干了这杯就散了吧 七月总有讲不完的树,喝不完的茶 爱不完的姑娘 和原谅不完的夕阳 走吧 路,还很长
◎淡蓝的从远外涌来
风标仍旧 凝固一样指向正北 沼泽上细碎的小冰渣依旧蚂蟥般 折腾她的脚踝 头巾下碎发仍旧 不时散落蹭疼酡红的冻伤 老迈的伯尔尼兹山地犬仍旧守护着它的羊群 在那个遥远的地名上,时间 都变得可有可无 唯有风 当它们吹透整个郡县时,湛蓝混合纯白天空 就回来。迷人的消息也会一 一传递过来
◎谁提着闪电的鞭子,谁就是我远方的人
作为一场思维的死亡 我承认,我才是最习惯缺席的那个 当你们坦露燃烧时,飓风就在隧道的另一端 当红蓼开始流淌出花蜜时,失望就坐在茶台边 而当游戏焦灼,言辞嘲讽时,我却笑了 面对满地碎裂的光,我的笑声 有些虚弱。把那朵梨花 迫不及待领到眼前时雨还没有来 你只是提着钥匙,站在 离远方和暴雨只隔一箭的地方 [img=800,240][/img] ◎比月光更大的雨一滴一滴落在石楠树叶子上
小轩窗内
芭蕉将影子
从午后一直摇到夕照垂暮
傍晚,风起
我对他说,易安的夜就要来了
比月光更大的雨
一滴一滴
落在石楠树
咚咚作响的叶子上
[img=800,240][/img]
◎黎明要出现的地方
在别处主角们又拿到风花雪月的脚本,在别处
人们竭尽全力
活出自以为令人艳羡的光
在别处,摇曳一再脱发的消瘦或臃肿
没来得及碎裂的露珠
会于正午前,袅袅娜娜飞升,在别处羽化
回应祈雨者的召唤
在别处
瑶光从天幕落回人间
会佩在腰间吗?问我的姑娘
如今,亦在别处
天,就要亮了
礼貌的鱼肚白,将依次濯洗着
那些即将到来的地方
◎多想在一块草坪上呆一下午
不去读南溟,那只杯子下的逍遥于自在
也不读长安,自半臂、幞头到后视镜里远去的树的纵深
游云未倦层风寐是我强加予风景的负累
手边叮咚作响的电话
又是谁予我的?
那接起后,又拨出去的呢?
◎想看你夜间的繁华
还,记得喊你方将的日子吗?
我说:嘘……别出声
那时候洱海奔跑着
苍山就停在月光下迎她
客栈,躺在我们身后,挡住了
来自城里裹挟迷迭香金酒与霓虹的风
而我们也许都不记得了——其实
那天月眉很细
风也很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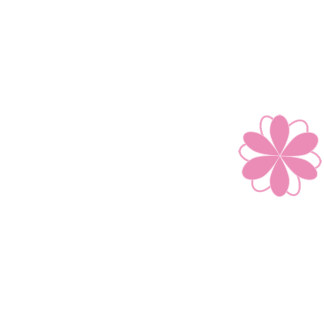
◎站在七月的肩膀上
不止七月
更不止流火
当时光可以成为借口后
就学会了谅解
自己
或另外一些自己
光阴,其实还算慷慨
会把青春还给渐渐老去的情歌
也会让人试着相信
这尘世
风很大时有花开,名曰半夏
◎同样都是大哭一场
当更细小的风吹再也无法撼动七月时
艾米莉记起漓江上撑篙的村妇
那双被戏称红斑绿绣手臂
藏在她
浸湿汗水的薄衫下
背后的故事,艾米莉曾在
那场她酒醉大哭的夜里对我提起
她说,比起红斑绿锈,她遇到的人就是枚君子
她还说,那个女人
竟然没哭
直到死去都一次没有
◎在中国,只有我窗外的荔枝是最甜的
从七月初,到
十月初
所有红色花朵都开了
而你却说
“所有的所有是个伪命题”
那么,在中国,这次我不说所有了
我说只有
例如“只有我窗外的荔枝是最甜的”你
并不反驳,指着窗外,说
周末我们去爬阴山吧
◎一群羊在乌鲁木齐走成一条河
哥告诉我
每年六月,走敖特尔的人
赶着羊
从星星低垂的地方过来
路太远了
他们会停下来抽烟、喝酒、打牌
羊也停下
躺在地平线上
哥又说
送信人走后就回了城里
在那儿
云朵和羊一样
躺在地平线上
长长的
|